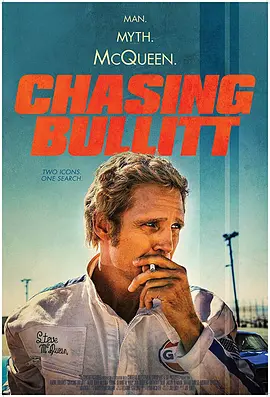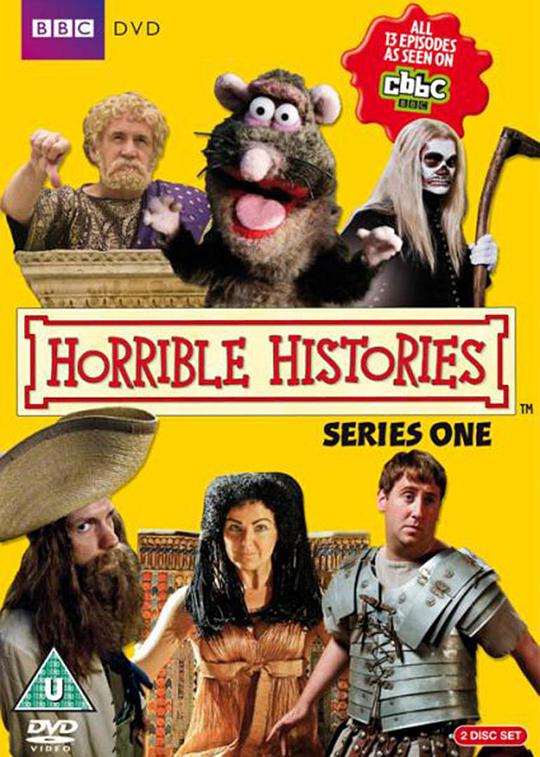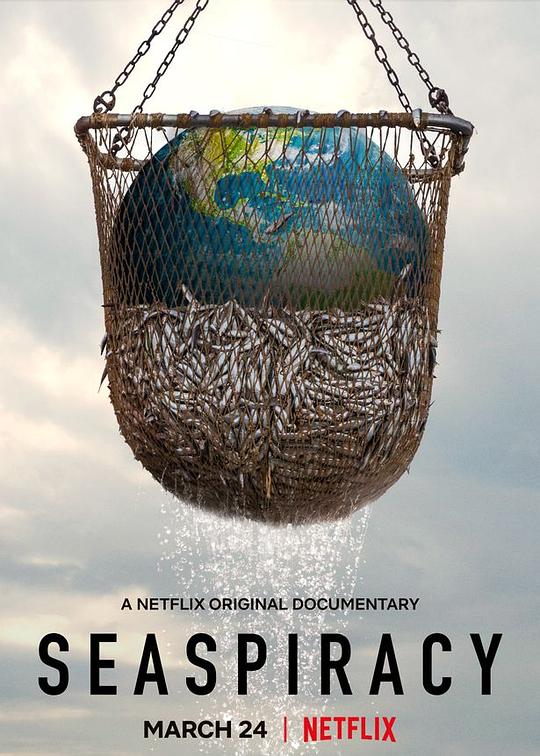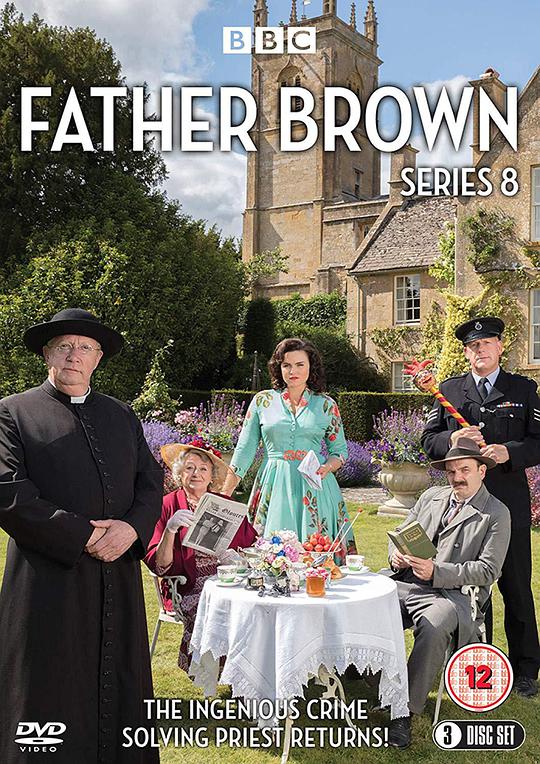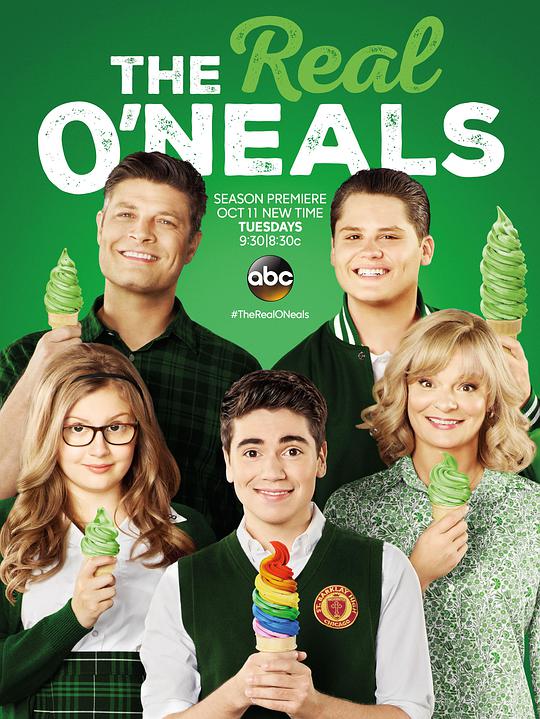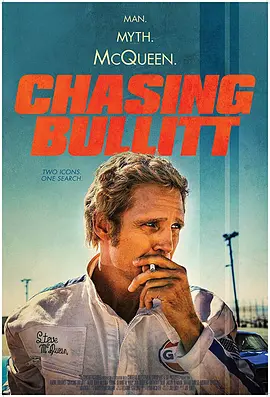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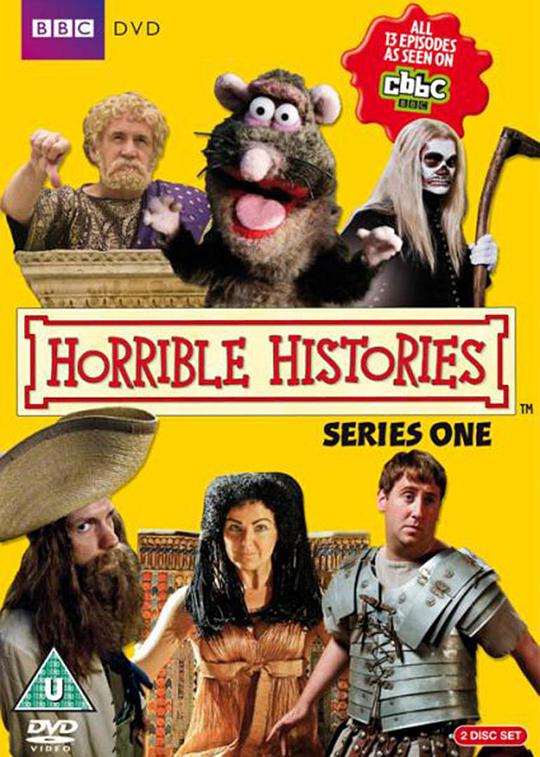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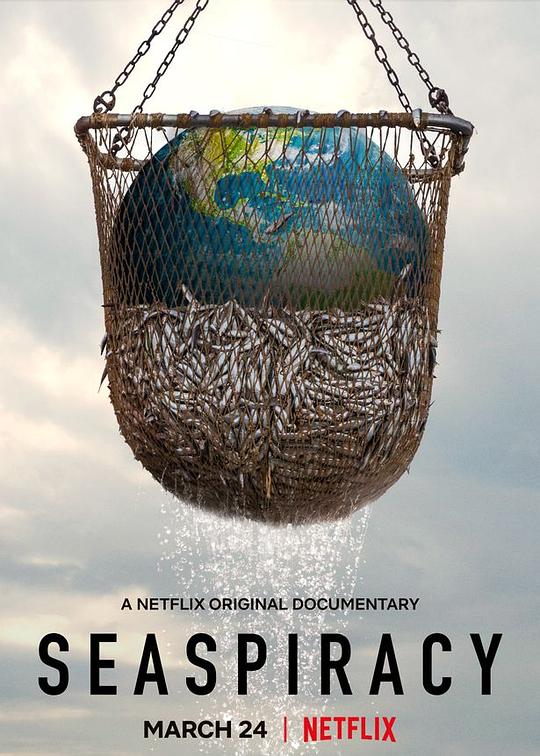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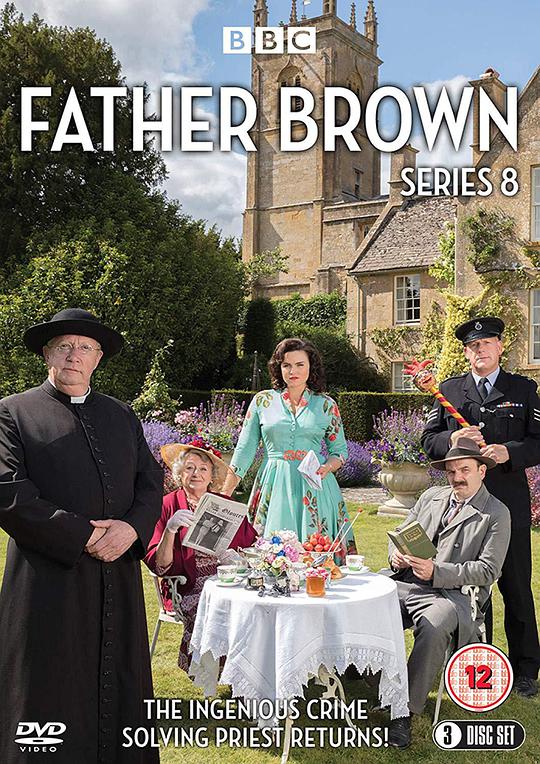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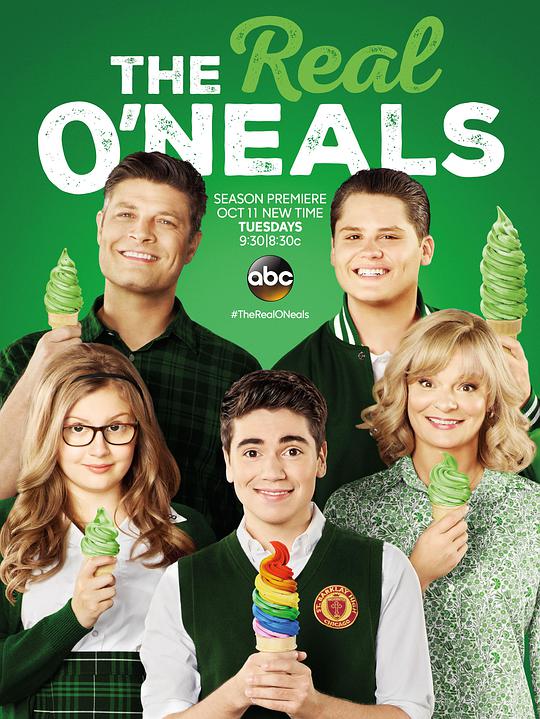











初冬,这时候的北海,像一块被岁月摩挲温润了的古玉。夏日的喧嚣和黏腻被一场接一场的北风,刮得干干净净,却还没有深冬那种刀削似的清寒。天是那种极高极远的淡青色,海呢,也不是盛夏时晃得人睁不开眼的钴蓝或翡翠绿,它沉静下来,变成一种更厚实、更接近于墨玉的苍青色,只在阳光直射的波峰上,碎开一粼粼慵懒的银光。风里有咸,但咸得爽利,混着阳光晒在礁石上蒸腾出的、微微的腥气,吸一口,直透到肺腑里去,把城市里积攒的那点浊气,涤荡得无影无踪。
你沿着北海银滩走,会觉得这世界忽然敞亮、安静了下来。夏天的这里,是沸反盈天的“下饺子”现场,花花绿绿的泳衣、尖叫、塑料泳圈,活脱脱一个漂浮的市集。此刻,沙滩却显出了它本来的、辽阔的静美。沙是极细极白的,被潮水一遍遍熨过,平整得像一匹刚刚织就的素锦。零星几个游人,影子被午后的斜阳拉得老长,在锦缎上缓缓移动,小得像几粒不慎遗落的棋子。海潮的声音也变了,不再是夏日怒涛拍岸的鼓噪,而是均匀的、沉着的呼吸,“哗——沙——”,一起,一伏,带着一种亘古的韵律。这韵律能催眠,你听着听着,心里那些纷乱的念头,仿佛也被这潮水一遍遍抚平、带走了。站在这空寂的海天之间,人忽然变得很小,小如一粒沙;又仿佛很大,大到能与这无边的静谧融为一体。这大概便是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点恍惚之境罢,在都市的格子间里是万难寻着的。
一、 海风穿过苏东坡的船舷
这初冬的海风,是有来头的。它不像春风那样带着暖昧的撩拨,也不像秋风那般满是萧索的杀伐。它清冽、直率,仿佛是从历史的缝隙里径直吹来的。闭上眼睛,我总疑心这风里,还挟着一千年前,另一个失意文人船头的叹息。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也是一个类似的冬天,六十岁的苏东坡从惠州再度被贬,渡海前往儋州。他必定是在北海(古称合浦)一带的海域经过,或许还曾泊舟暂歇。遥想当年,这位旷世才子站在颠簸的船头,望着同样苍茫的南海,心中该是何等况味?“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他诗中写的是琼州海峡的景象,但与眼前这片海何异?他看到的,不是风景,而是政治风暴后无尽的流放,是归期渺茫的“天涯”。海对于那时的他,是一道绝望的、深蓝色的壁垒。
历史的吊诡就在此处。如今这片让他心生“孤臣孽子”之悲的海,却成了无数人心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象征。当年那个“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的蛮荒瘴疠之地,今天已是楼盘广告里“滨海度假天堂”。海还是那片海,潮汐依旧,风云变幻。变的,是看海的人,和人所赋予海的意义。东坡先生若魂兮归来,看到银滩上林立的高楼、斑斓的遮阳伞,听到的不是惊涛而是观光游轮的汽笛,不知又会作何感想?是苦笑于命运的捉弄,还是慨叹“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这风从历史的深处吹来,吹过东坡的船舷,吹过疍家渔民破旧的帆,如今吹在我这个闲散现代人的脸上,清凉无别。它提醒我,眼前的繁华与安逸,并非亘古如斯。所有的“岁月静好”,底下都沉着厚重的、甚至是苦涩的时光之沙。在这静好的初冬里,能感受到这一层历史的凉意,或许是对这美景更深一重的领略。
二、 红树林:在咸淡之间
要看北海初冬最坚韧、最富哲学意味的生命,不能只在银滩的沙上看,得去城郊,去那些咸淡水交界的滩涂,去看红树林。
第一次走近这片林子,是有些讶异的。它们没有想象中的挺拔伟岸,枝干多是曲折的,甚至有些矮小敦实。但就在这其貌不扬之下,藏着惊人的生存智慧。最奇的是那些从枝干上垂挂下来的“气根”,直插入淤泥,像无数只坚定有力的手,紧紧抓住脚下流动不居的滩涂,任凭潮涨潮落,我自岿然。它们形成了迷宫般的支架,让整片树林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集体。
林下的世界更是精妙。退潮时,滩涂裸露,弹涂鱼(跳跳鱼)用它们强健的胸鳍在泥地上“行走”,两只鼓突的眼睛机警地转动,时而“噗”一声跳起老高;招潮蟹举着一只硕大得不成比例的螯足,在洞口耀武扬威,忙忙碌碌地搓着泥球。这些生灵,每日在咸水与淡水、浸泡与暴露、危险与安全之间,踩着精确的节奏生活。它们的一生,就是一部与潮汐博弈的微观史诗。
这红树林,不就是一种最高明的“中庸”哲学在自然界的显现么?它不选择纯粹的淡水河流,也不选择纯粹的汪洋大海,而是扎根于咸淡交汇、动荡不安的边界地带。它以柔韧的姿态应对冲刷,用集体的力量抵抗风浪,在“之间”的模糊地带,开辟出最蓬勃、最富饶的生态家园。这比起那些非此即彼、追求纯粹与极致的生存态度,是否更具生命的韧性?
凝视着这片沉默的林子,我想,一座城市的发展,或许也该有点红树林的智慧。不是在“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之间做单选题,而是在交汇处寻找动态的平衡。让高楼的长影与渔船的桅杆共存,让引擎的喧嚣里依然能分辨出咸水歌的旋律,让历史的根脉,以新的形式呼吸、生长。可惜,我们见多了简单的填海造陆,见惯了将复杂的生态与人文脉络,修剪成单调的观光步道。我们热衷制造“纯粹”的景观,却往往失去了那份在“咸淡之间”滋生的、复杂而旺盛的生命力。
三、 珠还合浦:寓言的光泽
初冬的午后,阳光暖和,适合去合浦的珍珠城遗址走走。这里如今只剩些断壁残垣,荒草萋萋,与不远处现代珍珠市场的热闹形成刺眼的对比。但坐在残存的土墩上,南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寓言之一——“珠还合浦”的故事,便随着咸风扑面而来。
《后汉书·孟尝传》里记载,合浦郡不产粮粟,而海中盛产珍珠。贪官污吏们“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贝便都迁徙到相邻的交趾郡去了,结果“合浦无珠,贫者饿死于道”。后来清官孟尝到任,“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不过一年,迁走的珠贝竟又“还”了回来,百姓重操旧业,商货流通,生活复归安乐。
这故事常被用来比喻东西失而复得,为政需清廉。但站在初冬的海边再想,它说的仅仅是人事么?珠贝何知廉与贪?它们所“感应”的,或许是一种更根本的秩序——生态的平衡与人心的安定。珍珠,这本是贝类应对入侵之痛的分泌物,是苦难的结晶,却因人类的贪欲,变成了招致更大灾难的诱因。当索取超越了自然的阈限,超越了公平的尺度,连这沉默的海中之物,也会用“离开”来表达抗议。而一旦秩序恢复,和谐重现,它们便又“归来”。这哪里是神话,分明是一则古老而深刻的生态寓言与治理寓言。
如今,合浦的珍珠多是人工养殖的了。在晶莹剔透的专卖店里,灯光下的珍珠熠熠生辉,每一颗都圆润完美,标着清晰的价格。我总觉着,它们美则美矣,却少了些传说中那“感于人事”的灵晕。那份在黑暗蚌壳中,因偶然的痛楚与漫长的忍耐而孕育出的、不可预测的光泽,被标准化生产所取代。我们得到了更稳定、更丰富的产品,是否也失去了与自然之间那份微妙而传奇的“感应”?
人工珠贝不会因为世道贪廉而迁徙,这或许是进步。但“珠还合浦”的故事,那份对“度”的警醒,对“和谐”的期盼,其光泽不应被现代性的强光所遮蔽。它应该像一颗真正的、古老的珍珠,沉在我们意识的深水之中,时时提醒: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对自然、对资源的索取,仍需怀有一份敬畏与节制。
四、 老街:活着的历史褶皱
如果说银滩是北海明亮崭新的面孔,那么珠海路老街,就是它一道深邃而温柔的皱纹。初冬的阳光斜射进这条百年老街,把两侧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在斑驳的墙面上缓慢移动,像一根古老的时钟指针。
骑楼是岭南沿海特有的建筑智慧。二层以上突出,跨建在人行道上,用立柱支撑,形成连贯的走廊。这格局,实用得很:烈日可遮,骤雨可避,方便行人,也更聚拢商铺的人气。细看那些墙壁,剥落处露出不同年代的灰浆,仿佛历史的年轮。窗楣上、山花处的雕饰,有中式的祥云瑞草,也有西式的卷涡玫瑰,洋派得很内敛,传统得很新潮。这是当年北海作为通商口岸,南洋风物与本土生活默默交融的证物。
如今的老街,自然是热闹的。两旁店铺鳞次栉比,卖虾饼的油锅滋滋作响,香气霸道;卖海味干货的,成串的鱼干、硕大的瑶柱在阳光下闪着暗金色的光;还有数不清的糖水铺、奶茶店、旅游纪念品摊。游客的喧哗,电喇叭的叫卖,嗡嗡地混成一片生活的背景音。
但这热闹底下,老街的魂似乎还在倔强地呼吸。你避进一条侧巷,喧闹立刻滤掉大半。偶见一位阿婆,坐在自家骑楼下的竹椅上,就着天光慢悠悠地择菜,脚边蜷着一只花猫。或是看到老理发店的旋转灯箱还在转动,老师傅用着最传统的推剪,给一位更老的顾客修理鬓角,动作慢得仿佛时光在此黏稠。这些瞬间,像是历史书页间无意保留下来的、活生生的插图。
发展与保护,在这里撕扯得最直观。政府挂了“历史文化街区”的牌子,修旧如旧,电线入了地,路面铺了青石板。可走进那些被精心修复的“示范”骑楼内部,往往已是装修现代的咖啡馆或精品民宿,原来的生活肌理被抽空了,成了精致的布景。这或许是一种必然的“活化”,但总让人觉得,那条真正活过的、气味复杂的老街,正在一点点退向记忆的暗处。
城市如同一个不断成长的巨人,需要新的血肉骨骼。但它的记忆、它的性情,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破旧的“褶皱”里。把这些褶皱全部烫平,换上一张光滑簇新却面无表情的脸,或许整齐划一了,但那还是“这一个”北海吗?在初冬温煦的光里,我漫步老街,觉得它像一位豁达的老人,不拒绝新潮的衣衫,也珍视自己身上的每一道旧痕。那份从容,恰恰来自于历史的深厚积淀。
五、 候鸟与人
初冬的北海,天空比其它季节更忙碌些。这不是云彩的忙碌,而是鸟的。大批的候鸟,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蒙古高原飞来,把这里当作南下越冬的中途驿站或终点。冠头岭国家森林公园、金海湾的红树林湿地,便是它们的天堂。
站在观测点,用望远镜看过去,场面是动人的。滩涂上,一大群黑腹滨鹬,像一片被风吹拂的灰褐色绒毯,倏然间整体腾起,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又齐刷刷落下,动作整齐得如同经过最严苛的训练。天空中,偶尔有苍鹭缓缓扇动巨翅,身姿沉稳,带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孤高。这些鸟儿,它们遵循着体内古老的罗盘与日历,年年岁岁,不远万里,来到这片温暖的海域。它们的存在,让北海的天空,连接起了极北的冰原与更南的热带,瞬间拓宽了这片土地的时空维度。
看着它们,我忽然想到,我们自己,不也是另一种“候鸟”么?尤其是这几十年,从各地迁徙而来,在这海滨城市落脚、谋生、安家的人,数不胜数。我们追逐的,不是季节性的温暖与食物,而是人生的机遇、更宜居的环境,或仅仅是一个“面朝大海”的梦。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筑巢,努力生根,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也被城市所改变。
鸟的迁徙,是自然的律动,纯粹而悲壮。人的“迁徙”,则夹杂了更多的计算、梦想与乡愁。鸟群年年往返,路线或许恒定。而许多来了的人,便不再离开,成了“新北海人”。他们的乡音混杂,口味交融,让北海的底色,在疍家文化、岭南风情之上,又添了天南地北的调料。这座城市,因此而变得更加有层次,更加“杂糅”,也更加充满不确定的活力。
黄昏时分,鸟群归林,发出阵阵喧鸣。城市华灯初上,车流如织,那是另一种归巢的信号。自然的韵律与人类社会的节奏,在这一刻,被暮色温柔地笼罩在一起。或许,一座理想的城市,就应该既能安顿这些远道而来的翅膀,也能抚慰那些漂泊寻觅的人心,让所有生命的迁徙,都能找到一个温暖的、值得停留的港湾。
日头渐渐西沉,将海面染成一匹巨大的、抖动的紫金色绸缎。风里的凉意更重了,分明是初冬的质感。我离开海边,往回走。身后,潮声依旧,不紧不慢,仿佛在吟诵一首无始无终的长诗。这初冬的北海,它不给你看它最热烈的容颜,也不展示最严酷的考验,它只是平静地、丰厚地展开自己。在它的平静里,你能听到历史的回响,看到生命的智慧,触摸到发展的脉动,也照见自身的来路与归途。
它是一片海,也不仅仅是一片海了。(黄胜余、朱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