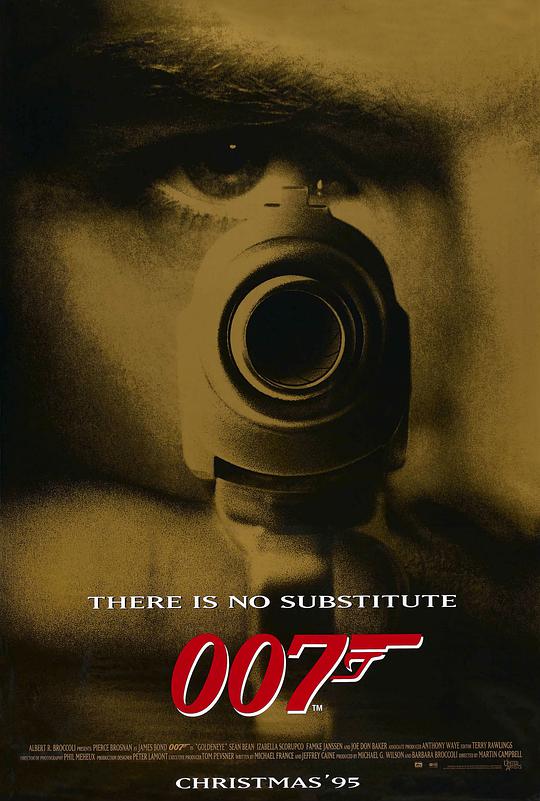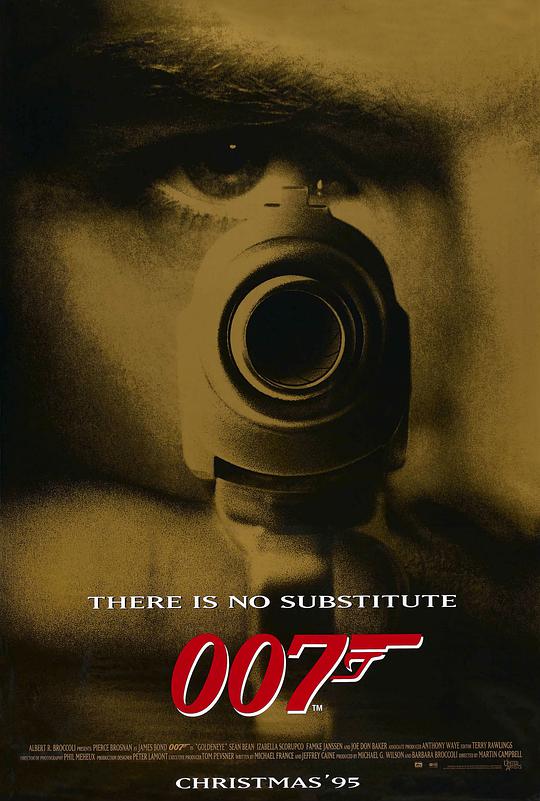




















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在准备访问耶路撒冷时,安排人在这座城市的古老城墙上开掘出一座特殊的入口。德国皇帝骑着一匹黑色骏马,身穿戴满勋章的军服,从这座城门进入了老城区(全世界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地),活似一位现代的十字军征服者。
这个做法给德国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公共影响,于是英国人在1917年12月胜利进入耶路撒冷时,努力做得低调一些。严格遵守马克·赛克斯(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政治上的舞台经理)在千里之外发来的建议,英军的决定是让艾伦比将军徒步从城市的一座传统城门进入,并且不展示英国旗帜。赛克斯指出,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协约国获得了宣传上的一个极大胜利,任何带有英国或基督教获胜而洋洋自得意味的东西都肯定会破坏大局。
T. E.劳伦斯碰巧也参加了12月11日上午进入老城区的历史性游行。在德拉的悲惨经历之后,他返回了亚喀巴,随后被传唤到位于巴勒斯坦南部的艾伦比野战司令部。他在前往那里的途中以为自己一定会因为雅莫科行动的失败而受到斥责或甚至是贬黜,但艾伦比对他的一连串战斗胜利相当满意。12月9日,他还在总司令部的时候,消息传来,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在撤离耶路撒冷。他借了一套军服和适当的军官肩章“星星”,换下了破破烂烂的阿拉伯长袍,扮作克莱顿将军的参谋军官,加入了入城游行队伍。尽管劳伦斯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所剩不多,但还是被这一天的重大意义所震撼;六百多年来,第一次有一支欧洲军队返回了西方宗教的摇篮,中东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来说,”他后来写道,“这是战争的巅峰时刻。”【24】
劳伦斯无疑还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感到深深震撼。在11月末,他一瘸一拐地返回亚喀巴,疾病缠身,而且因为在德拉遭受的虐待而十分羸弱的时候,他才得知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取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得知《贝尔福宣言》的存在,以及导致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俄国革命。在离他更近的地方,他还错过了宿敌爱德华·布雷蒙的最终失宠。
自当年春季以来,英国一些高官就在打算要搞垮布雷蒙。事实上,对布雷蒙的憎恶是劳伦斯和马克·赛克斯少数共同点之一。“我坚信不疑,法国军事代表团越早离开汉志就越好,”赛克斯在5月给外交部的信中写道,“法国军官们无一例外,都是反阿拉伯的,只能造成争吵和阴谋。”赛克斯认为,法国人的这种敌对基调是由法国军事代表团的领导人定下的,源自“布雷蒙上校遵循的刻意乖张、刚愎自用的态度和政策”。【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恰恰是赛克斯对布雷蒙的批判让这位法国上校得以继续留下很长一段时间。巴黎方面得知英国人对布雷蒙的恶感之后,为了避免显得自己对盟友俯首帖耳,答复称,非常凑巧,他们已经在考虑缩减布雷蒙的吉达代表团的规模【26】。显然是为了制造一个给法国人台阶下的“体面的时间间隔”,好让大家相信裁减代表团的主意是法国人自己想出来的,于是在随后六个月内什么都没做。英国官员们在这场哑谜中也扮演自己的角色,利用这段时间研究要给讨厌的布雷蒙颁发一个什么荣誉头衔。最后决定是“最卓越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于是雷金纳德·温盖特利用给布雷蒙授勋的机会,向他表达“热烈的祝贺和赞扬,感谢法国代表团在您指挥下在汉志所做的价值极高的工作”。【27】
爱德华·布雷蒙虽然获得了英国最高级的军事荣誉之一,但说到底他仍然是个法国人。被撤职的上校启航返回法国的时候——为了给他留面子,官方的说法是他要度六周的假期——温盖特向外交部的一位高官发了一封电报。“布雷蒙之前的事迹你是知道的,”他写道,“我想,他这次回国的主要目标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是探查巴黎公众对皮科和赛克斯的协约国政策的意见。应当向赛克斯发出警告。”【28】
布雷蒙的退场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在中东的活动就告终了。恰恰相反。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取胜之后,原先只是理论上的瓜分中东战利品的计划现在变得触手可及了。游戏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因此政治阴谋将会比以往更加活跃。
12月11日,耶路撒冷入城式结束之后,英国司令部高级人员来到一座宴会厅用午餐。劳伦斯在这里窥见了即将扩展的政治阴云。作为常驻艾伦比司令部的法国政治官员,乔治—皮科在入城式中享有贵宾地位,他显然认为,这说明他和马克·赛克斯在两年前制定的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共管的计划依然有效。在宴会厅,皮科对艾伦比宣布:“亲爱的将军,明天我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城里建立民事政府。”
按照劳伦斯的说法,这句话让宴会厅陷入了难堪的沉默。“我们湿漉漉的嘴里含着色拉、蛋黄酱鸡肉和鹅肝三明治,停止了咀嚼,我们目瞪口呆地转向艾伦比。就连他在那一瞬间似乎也不知所措。”【29】但只是一瞬间而已。艾伦比转向法国政治官员,解释道,由于耶路撒冷位于英国军事区,城内唯一的领导者应当是军队总司令,也就是他本人。
翻天覆地的战局让法国人对英国施加了新的压力,但这只是英国人面对的政治麻烦的一小部分而已。耶路撒冷入城式之后,劳伦斯又去了开罗,亲眼目睹了那些政治问题。他看到的开罗是一座陷入狂怒的城市。
马克·赛克斯原先认为,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不会让阿拉伯人不悦,但现在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尽可能封锁消息,不让阿拉伯世界得知《贝尔福宣言》的情况。他的努力以惨败告终,《贝尔福宣言》的消息在11月传到了埃及群众当中,沮丧很快变成了愤怒。英国当局努力去安抚这些抗议者,但杰马勒帕夏的贝鲁特讲话又揭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具体条文。电光火石之间,英国人努力将阿拉伯世界拉拢到自己这边的长期努力遭到了惨痛的双重打击,其后果可能会使得艾伦比在巴勒斯坦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
劳伦斯在开罗静观局势,预感到黑暗的日子即将降临。如果一向唯唯诺诺、受到严厉管制的埃及群众都被《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科协定》激怒到几乎要揭竿而起,那么聚集在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和他们在叙利亚各地的潜在盟友会怎么想?劳伦斯私下里感到一丝安慰,因为他很有远见,早在九个月前就将《赛克斯—皮科协定》告知费萨尔;如果费萨尔是现在才知道的话,再加上《贝尔福宣言》恰好也在这时被披露,他恐怕很难再信任劳伦斯或任何一个英国人了。但这些消息一定会让在亚喀巴围绕在费萨尔身边的人火冒三丈。不管他们对费萨尔或者阿拉伯独立事业多么忠心耿耿,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直有个想法,即起义的哈希姆领导人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被英国和法国主子愚弄了。当然了,君士坦丁堡一直是这样说的,现在杰马勒帕夏在贝鲁特的讲话给了这种指控更强的说服力。
在开罗,劳伦斯很快得知了费萨尔所处的困境,以及杰马勒向他提议的脱身之路。
11月底,费萨尔收到杰马勒的和平提议信之后,将其副本发送给了父亲。12月中旬,侯赛因又将信转发给了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侯赛因这么做或许是为了表示,即便到了此时,他仍然信任英国人;或许他这也是个警告,即如果英国人敢骗他,他还是有其他路可走的。当然了,他或许是认为,英国人肯定很快就能自己发现这件事,因为杰马勒在他的贝鲁特讲话中提及了对阿拉伯起义军的和平建议。
不管侯赛因的动机如何,他交出杰马勒的信的举动让英属开罗大为警醒。几天前,克莱顿就向赛克斯警告说,现在《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消息已经在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土耳其人向起义军提出媾和建议只是时间问题【30】。杰马勒的信表明,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好在费萨尔和侯赛因都没有对这个提议作出回应,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即告知英国当局。但谁知道土耳其人下一次发出提议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劳伦斯的看法则与此大不相同。事实上,他认为,杰马勒帕夏的信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带来了一个独特机遇。
正如在10月份劳伦斯向乔治·劳埃德吐露的那样,他认为自己不是在为英国效力,而是为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工作。在开罗的英国军方和政界高层,人尽皆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英国使节一直在瑞士与土耳其使节会谈,商讨议和事宜。既然英国可以毫无道德顾虑地与敌人秘密谈判,那么阿拉伯人为什么不可以?恰恰相反,阿拉伯人可以打一打土耳其这张牌,或许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特定的条件,随后也许能够从英法方面得到一些具体的让步。如果牌玩得好,或许不管谁赢得战争,阿拉伯人都能得到独立。
劳伦斯当然不会把这些想法明说给他在开罗的上级们。他只是告诉他们,符合英国利益的做法或许是,搞清楚土耳其人愿意给阿拉伯人开出怎样的条件,这样英国人就可以先发制人地作出反应。这个说法虽然没有说服力,却得到了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支持。“我建议侯赛因国王不向土耳其人作任何正式回复,”温盖特在给战时内阁的电报中写道,“但劳伦斯少校会询问费萨尔,是否可以请费萨尔与杰马勒交换口头消息,以摸清土耳其的新政策。”【31】
战时内阁迅速行动起来,驳回这个建议,但他们的动作还不够快【32】。就在温盖特发出电报的当天,即圣诞节前一天,劳伦斯已经离开开罗。到战时内阁插手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亚喀巴,在费萨尔身边了。就像他之前在其他关键时刻做的那样,劳伦斯利用收到命令的延误作为借口,自行其是。他鼓励费萨尔与土耳其敌人对话。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费萨尔和劳伦斯与叙利亚南部战线的土耳其总司令建立和维持了这样的对话【33】。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费了很多心思来努力为这些通敌行为辩解,声称土耳其政权已经分裂为两个阵营,即杰马勒帕夏那样的伊斯兰教徒和叙利亚南部战线总司令那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费萨尔或许可以在两个阵营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对其矛盾加以利用。劳伦斯写道:“借助精心选择的措辞,我们可以将阿拉伯起义归咎于杰马勒的教徒派,或许军国主义派会和他们闹翻。”【34】他的理论是,最终这种闹翻会对阿拉伯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赢得独立,后者可以解放自己的手脚,集中力量保卫自己在安纳托利亚的家园。
劳伦斯或许是认识到自己论点的缺乏说服力,后来努力将自己与此事拉远距离。在1922年的所谓“牛津版”《智慧的七柱》中,还是“费萨尔在我的全力支持下,向杰马勒发回了有目的性的回复”;而在1926年版《智慧的七柱》中,就变成了费萨尔自行决定与敌人谈判。【35】
三年后,劳伦斯提出了一个更为简单,但也更为老掉牙的解释,为自己与费萨尔的行为辩护。不是别人,恰恰是威廉·耶鲁在1929年向他问起了战时那些与敌人联络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在爱情、战争和联盟中,大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是公平的!”“噗!”【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