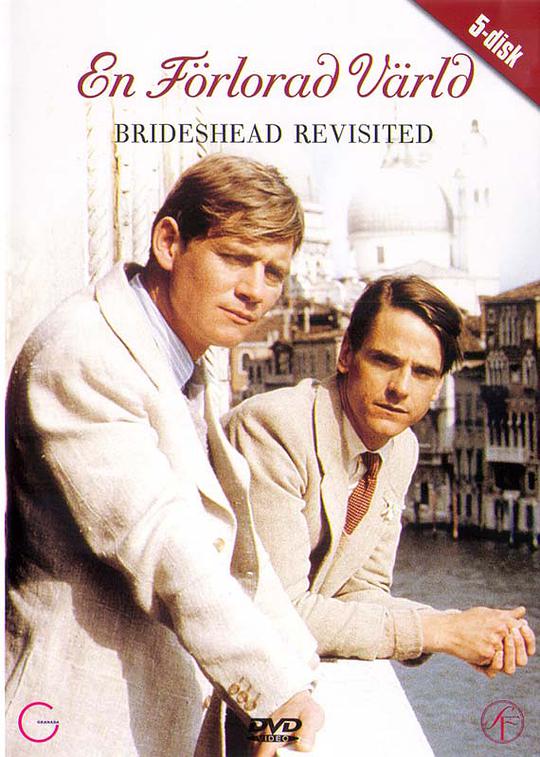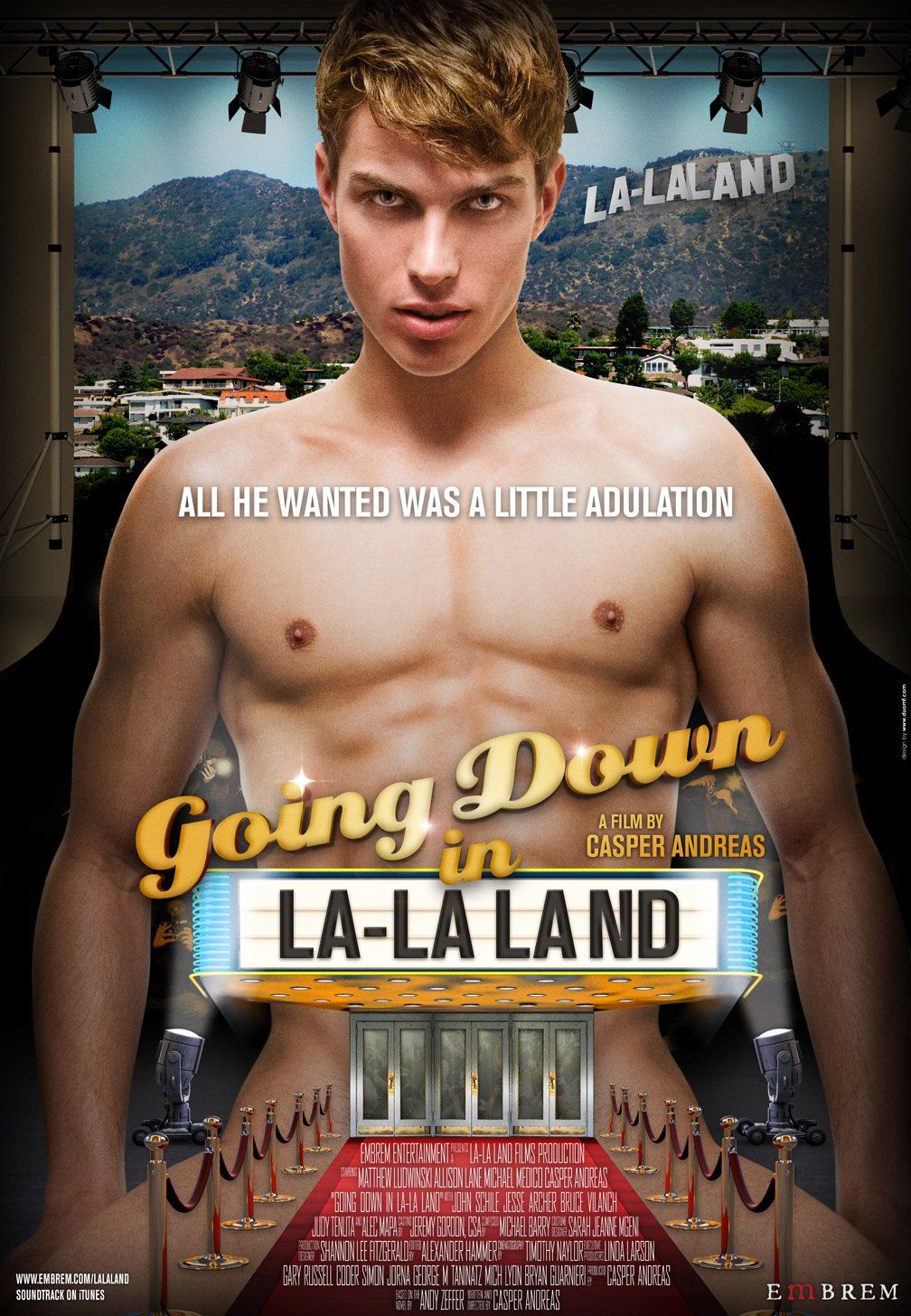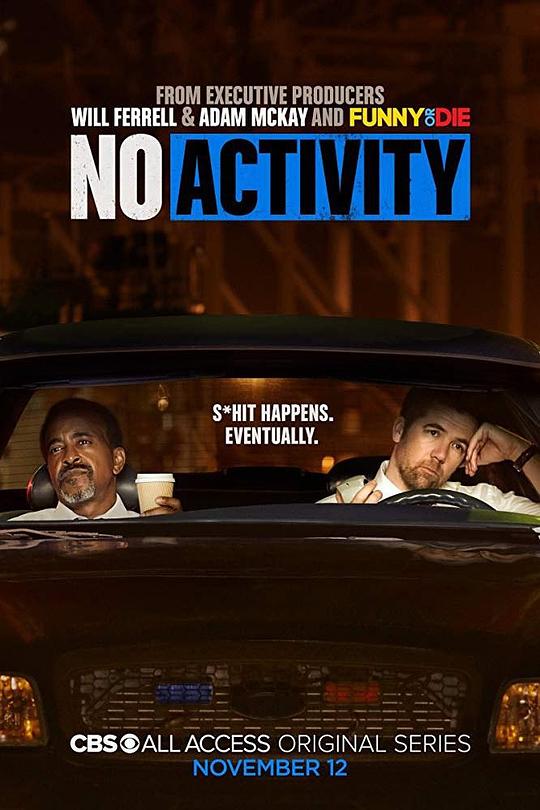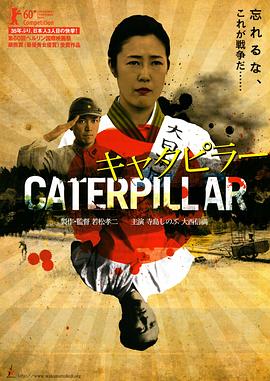191期主持人 丁欣雨
这段时间,一则视频在社交媒体发酵,视频拍自11月底在上海举行的中文播客大会,标题为:毛尖和许知远现场吵起来了。
点开视频发现,在这两位文化圈名人现场言辞针锋相对之前,并未产生直接交谈,只是在应对同样的提问时态度有些错位,当被问到这一年做了什么事情,许知远回想起前一天阅读马尔克斯谈话录令他洋溢的“美好期待和柔软幻想”,而毛尖分享了她国庆摸一手好牌却打到稀烂的故事。
但渐渐地,两个人都开始表现出对彼此态度的不认可,许知远称接地气的发言风格在当下这个社会越来越“通货膨胀”,人们把粗俗当作是一种真诚创作。在他看来,俏皮的语言或许能给人带来释然,但更深层的意义会被即兴一笑瓦解;毛尖反过来质疑许知远词汇里频繁出现的“少年”“梦”“哭泣”也同样在踩中流量密码,她转向许知远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好像配不上你,但我很喜欢这个时代。”

我们无意延续这场辩论的站队,但二者的矛盾令人不禁想要追问:这个被毛尖拥护、又配不上许知远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我们看到文化名人携带着强烈的身份标签出现在意见空间,并主动为自己可被识别的风格做出辩护时;当他们的立场的确代表了两种分道扬镳已久的审美倾向,深沉文艺失去往日威严,越发不被看好,而朴实俏皮正占于上风时,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王鹏凯:许知远在《十三邀》里有一场对谈很出名,他跟李诞吃烧烤,李诞问他:“你平时说的书真的都看过吗?还是说你只看了别人写的书评,就在那边评论了?”许知远很坦诚地说:“有些书我没看过,我就是看书评。”当时李诞让许知远不要把这个话说出去,不然会被骂的,但许知远认真回应他:“我觉得有些好的书评比书本身还要好。”
许知远不会觉得大众讨厌这件事,他就不去讲了,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个性给表达出来。他有自己审美上的趣味,他也把这种趣味作为标签打出来做他的节目,没有在刻意讨好当下这个时代。
李欣媛:许知远的采访嘉宾如果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洽谈一般来说就会比较顺滑,但是如果许知远对谈的是影视圈的人,那么争议就会出现,比如说李诞、马东这类“游戏人间”的人物,让许知远会有一种拳头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

许知远不会顾及很多,他直白地说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蛮珍贵的,但有时候他会有一种天真在里面。比如他和俞飞鸿,还有和木村拓哉的谈话,都非常不共频,他执着追问“你是怎样的,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能感觉到许知远信仰的东西在得不到回应时好像变得很无力。
很多时候可以发现他们的主题延伸到最后,就是你要听“远处的哭声”,还是要听“近处的哭声”。许知远选择的是前者,而其他嘉宾选择的是后者。影视圈沾染到的商业气质,或者说面临的挑战是更多的,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淬炼了,包裹起来了,会觉得很多东西是不值得的,是没必要的,他们会觉得许知远所代表的抱负离自己已经太遥远了。
张钊涵:我想起鲁迅有一篇文章说,“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最近网络上也有人引用这段话概括这次争论,我想这是不准确的。我去看毛尖B站的页面,简介是罗岗的一句玩笑话“为人民看烂片”,她说现在的电视剧和电影是中国最封建的地方,财富按照颜值分配,她也会质问大资本和产业结构,甚至批评奥斯卡奖的分配,但从不质询那个显而易见的、更根本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有点可疑的。

许知远的方式更加隐秘,他确实说中了一些社会弊病,我也相信他足够真诚,但他觉得自己是李普曼,并不信任公众,他的落点在于这个时代变了,变得“配不上我们这些悲天悯人的写作者”,这又倒退回审美的逻辑,其实有点自怜。
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会议,作家李陀提到现在的文艺批评和媒体写的东西太过学院化。他认为很多批评家不再批评了。现在的情况是,出现一个新电影,我喜欢就来夸一夸,如果不喜欢,商业片拍得不好我就说这是个文艺片,文艺片拍得不好就去骂白左和政治正确过了头。他说这个时代唯一一个批评家就是写影评的毛尖,无论毛尖的说法正确与否,她至少还在批评,而这正是批评家的第一要务。
许知远和毛尖的讨论本身就构成一种症候,这代表公共讨论空间的萎缩。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文艺的想象就是许知远了,对于批评家的想象就是毛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公共的声音是不够多元的?
丁欣雨:毛尖前些年出了一本剧评集《凛冬将至》,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写了篇序言,标题叫作《毛尖本色》,她提到毛尖是一个多面孔的人,但她用毛尖在某个大奖发表的一段获奖感言,来解释她认为的毛尖本色。
当时毛尖说,“我的写作动力是源于那些来自我们成长年代的高尚愿望,那些被今天的生活所屏蔽掉的很多词汇,如果还能够感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感动更年轻的人呢?本质上,我们与万事万物有着更家常的潜在情义,我们是通俗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平庸的时代造就了我们,而我们全部的工作就是改变这种平庸,直到时代最终把我们抛弃。”

这就像钊涵讲到的,毛尖虽然跟日常生活的连接更加紧密,但她依然有想去批评的东西,但在这场活动的争吵里,她差不多完全把自己放在了许知远的对立面,而没有谈到更加深的她有所坚持的东西。
毛尖作为一个多面孔的人,她的本色到底是什么样的?贺桂梅认为的毛尖本色会不会只是她想要从毛尖身上看到的那一面,而我们每个人想从这些在公共空间发表意见观念的人身上看到的本色,可能都对应着我们的期望,他们变成了我们想要在网络空间看到什么的投射,而在这场播客大会的活动上,我们正好需要这样一个面孔的毛尖?
丁欣雨:现在的学者除了主动发声,很多还会被拉去提供其他功能。比如如果最近有影视作品跟什么议题相关,就会找学者参与首映活动,邀请学者是想要达到用理论背书来宣传文化产品的效果。
李欣媛: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也是在给学者强化各种各样的标签,以此来希望他们的观点和自己作品的主题达成一种契合。比如要办一个关于剧集的活动,就去找毛尖,要是办一个女性的活动,就去找戴锦华,办一个法律的活动,就去找罗翔。
张钊涵:我感觉学者的公共发言有两种,一种比如说和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话,大家会骂你歪屁股,很多是人身攻击。还有一种是你说了几句话,媒体或者主办方觉得很好,截出来给你做一分钟的切片,每个人都在夸你,说你真是金句制造机,真是人间清醒,但这个东西非常碎片,省略了整个论述的过程和当时聊天的语境。目的也不是提供什么信息,而是想让你知道你的情绪我懂,所以你愿意去转发,本质上还是消费增值的逻辑。

这种无奈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很难有真正的批判。平台资本有自己的代言人,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本身已经面临危机,他们一边批评金钱至上和世风日下,一边发现自己曾经奋力反抗的对象消失了,不再有具体的敌人,只剩下一种神圣的道德姿态。毛尖和许知远的讨论把重心放在“时代”是有问题的,他们都很取巧地回避了知识分子整个阶层滑落的原因。
王鹏凯:播客《读笨书Read or die》有一期节目叫“从项飙到袁长庚,谁能为当代生活做注”,讲的是当下一些学者在公共空间的表现,里面有提到袁长庚,他是现在国内公共发言最活跃的人类学学者之一,很多人文相关的活动都会看到他是活动嘉宾。袁长庚包括之前的项飙,其实跟前面我们讨论这么多的名人一样,还是知识分子维度的,不是真正的流行文化,但他们为什么会在简中互联网如此受欢迎,是因为相较于其他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更贴近大众,或者说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更容易被这个时代的公众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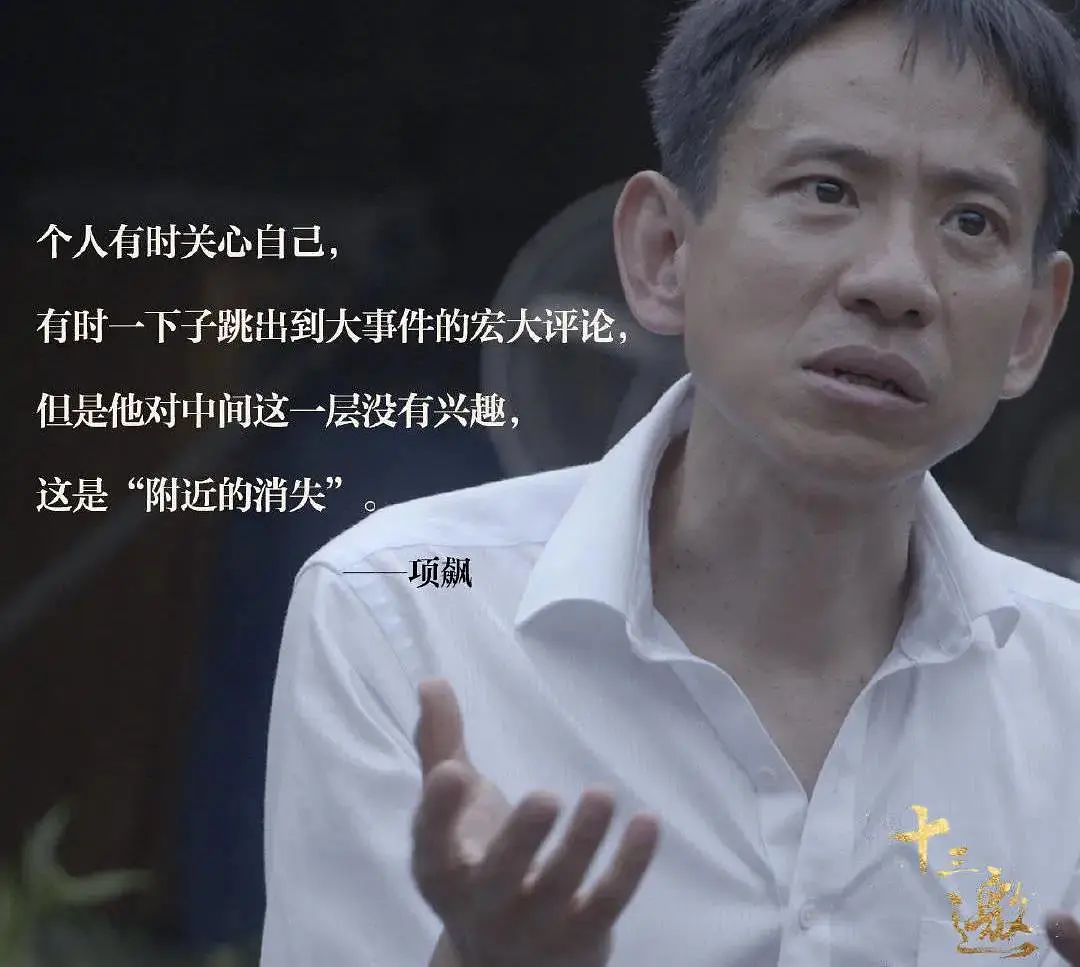
当下的观众想要获得对自己生活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又必须以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观众的接受度其实是有限的,你需要在安全范围内讲出这些话。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可能就会受到批评。
我认为毛尖就不是一个所谓“俏皮通货膨胀”的人,她其实非常聪明,做B站账号短短一年时间就积攒了非常高的关注度,她很清楚在舆论场里面说什么话,既能够显得自己很犀利,同时又很安全,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安全范围,她是能很精准地把握它的,这种人其实在当下很少。
丁欣雨:《中国新闻周刊》发了一篇文章,写到最近小红书有很多文化名人起号,发布一种AMA(我是xxx,ask me anyting,有问必答)的内容范式,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提问,生活太苦了怎么办?天气冷心情差怎么办?他们亲自下场一一解答,运用一点知识,也会用幽默表达来回应他们。这大概也能对应上许知远所说的“接地气”吧。即使是拥有很多知识储备和文化资本的名人,我们跟他们的距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有平凡亲民的一面。

《纽约客》一篇文章(The Scourge of "Relatability")说到,接地气的泛滥,需要警惕的在于,如果我们频繁要求一个人或者一个作品是接地气的,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期望:希望这个文化产品或者名人言论是反映观众体验的,希望作者可以替我们发声。这个时候他们只是被视作获得自我认同的一面镜子,从中你可以认出你自己,但这是一种极其片面的体验。“如果仅仅因为我们觉得某部作品无法以我们能够轻易辨认的方式反映自身,仅仅因为某部作品需要我们积极动用想象力或唤醒同理心,就否定它,是我们自己的失败。”
丁欣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这本书里讲到国外语境的一个术语叫作“流行文化拥护主义(poptimism)”,一开始出现在音乐领域,长久以来大家觉得摇滚或是类似的音乐形式是更加高尚,更能有音乐批评的空间的,但像流行音乐和口水歌之类,文化价值是被贬低的。
流行文化拥护主义就是在对抗这种摇滚主义(rockism),指出一些人喜欢摇滚,并不是真的热爱摇滚乐,有的时候是把摇滚简化成一种漫画化的形象,作为炫耀或者标榜自己身份的标签,另一方面也有身份政治的原因,过度关注高雅艺术,会疏远一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还会通过否定他们的品位来给他们造成实际伤害。流行文化拥护主义宣称不应该存在所谓的高雅和低俗文化,我们只有文化。
书里讲到一个转向的例子是星巴克,一开始这种流水线式的连锁咖啡店铺被人批评,他们会去喝手冲,或是找到更稀罕的咖啡豆来抵抗这种千篇一律,但到现在很多人又正是因为星巴克是基础款而去重新喝回它,因为这才是更贴近现实和大众的饮料。抵抗所谓精致稀缺的审美是当下潮流的一部分。书里也发现,俗咖原本是用来贬损文化审美品位很低的负面词汇,但现在会有一群人主动用俗咖来标签自己,作为一种自我赋权的方式,我感觉周围确实有这种倾向,跟许知远说的“把俗当成一种真诚创作”也能呼应上。

李欣媛:这种讨论我在电影节的活动上经常会看到,有的创作者觉得我们要迎合观众,要拍观众喜欢看的东西,但另一部分人就觉得我们要寻找观众,不能让观众的看法来影响我们的创作,这两派有的时候更趋近于商业片和文艺片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偏移了,一些人指责粗俗,有的时候这会驱使他们把一些东西弄得玄而又玄,这种现象正在蔓延。我在跟一些非常年轻的青年创作者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这种意识非常明显,一直在讲风格艺术、内在情感,停不下来地自我感动,跟他们聊着聊着,我就会陷入一种虚无的状态。
张钊涵:我想补充一下从文化知识领域角度讨论这件事的语境。中国90年代的开启很曲折,有些人觉得在社会氛围没有改变之前,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不会有什么作为,当时有个亲历者的说法是,在政治上知识分子无所作为时,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方式去安放自己的道德热情。学术语言的开始,或说学术专业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一代人惯用的欧式长难句,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现在学院里的一些青年老师,他们的语言依然是上一两代人的模样,他们受到教育的全部就是习得这样一套语言。这些人的公共发言也不是出于真诚的困惑,而是为了完成师承下来的题目,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媚俗呢?至少这是个很常见的投机方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公共发言的力量,无一例外都是五十岁往上的人,这里有一个代际问题,如果年轻一代没有能力直接回应社会问题,还执着于用学院内的写作方式介入社会批评,那么知识分子的想象恐怕还要被许知远和毛尖占据。
王鹏凯:我前两天看Netflix拍的《纽约客》100周年纪录片。《纽约客》一直以来受到的一种批评是,觉得它太精英主义了,在纪录片里,《纽约客》的一些作者回应了这个质疑。

其中一位是当下很受欢迎的非洲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她指出,很多对于精英主义的批评容易滑向一种反智主义,这是需要警惕的。她说,如果我们用一种复杂且深思熟虑的方式写有关艺术、文学和政治的文章就是精英主义,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去求真,想要听到不同方面的声音,这种对于深刻思考的追求就是精英主义,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精英主义。阿迪契的观点还蛮坦诚的,精英主义不一定就是负面的,它也处在话语的争夺中。
王百臻:前几年曾经流行过一个词,叫“祛魅”,在与祛魅相关联的帖子下面,我所观察到的是,这个说法很多时候指向了某种对精英主义范的、高度封装的深层符号系统的解构。这样做首先确实构成了一种“扳正”,其让人能够正视日常的文化消费模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融文化的阶层之别。但另一方面,只依赖这样的工具或许又会在另一个层面阻隔对话的发生,同时助长一种新成见。
譬如说,在文艺片和现代诗等重灾区中,当我们遇到看不懂的东西,往往会快速形成或依赖一套所谓的“祛魅”话语,把某个对象粗暴地简化为资本主义的游戏,或者是“圈内人”的自嗨,指责其愚昧大众,而非真正拥有某种意义。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刚才提到的“一切文化不分高低”当然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但我们或许依然要警惕,在向这一目标努力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另一种简单粗暴地拒绝对话、拒绝理解的矫枉过正的倾向。